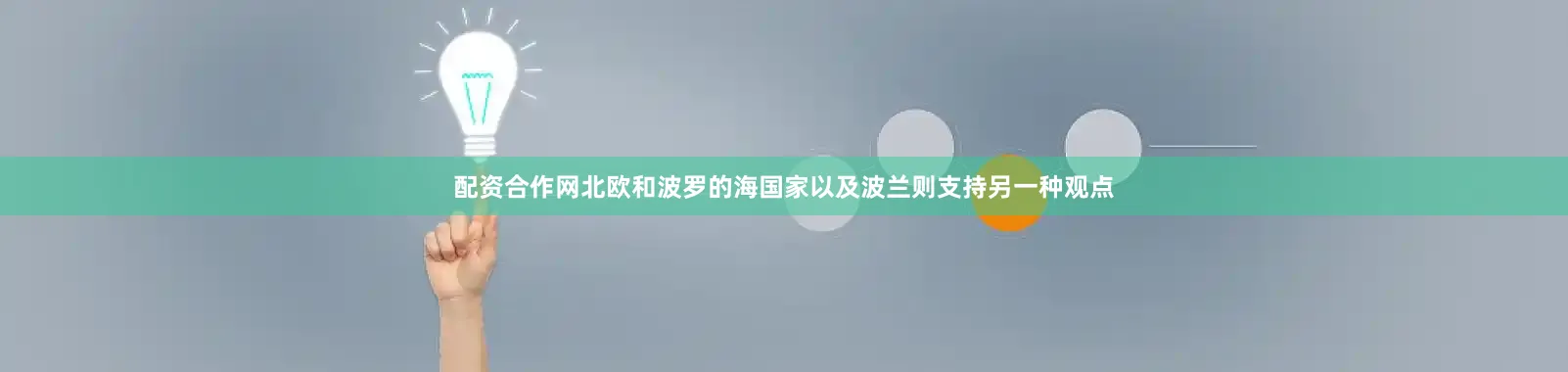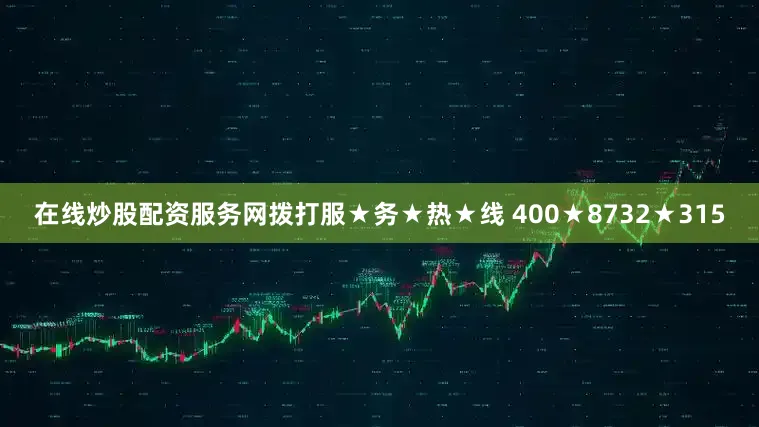【内容合作/留学咨询 | 微信号:yizhili2019】
采访的这天,Alice要请我们喝奶茶,说辛苦我们采访她。后面发现她其实拎了六杯奶茶,而我们只有五个人。
“你是不是算错人了?”我问。
她笑了笑说:“没有啊,多买了一杯的。”
我有些好奇,“为什么?”
她想了想,说:“我妈从小就教我,做事要多替别人考虑一点。如果临时有人加入,或谁忘了点,就不会尴尬了。”
那一刻我更加欣赏Alice了,这个松弛自信、偶尔会自嘲是“P人”的女孩,内心有一种非常细腻且稳定的感知力——不是表演出来的体贴,而是一种融进性格深处的对他人的敏感和关怀。而她的设计,也是这样开始的。
—— 小编前序
展开剩余94%Alice同学
康奈尔大学|本科|Information Science
康奈尔Connective Media、康奈尔Design Tech
加州伯克利MDes、纽约大学ITP和宾大IPD等offer
康奈尔“村”
学习生活很开心
“
我很喜欢康奈尔。这个地方因为够偏,所以朋友之间的关系特别近。在康奈尔,人与人之间有种‘一直在场’的温度。
”
Alice 本科就读于康奈尔大学 Information Science(信息科学)专业。在刚刚结束的硕士申请季中,她凭借扎实的学术和清晰的方向,一举拿下康奈尔 Connective Media、Design Tech,加州伯克利 MDes,纽约大学 ITP,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 IPD(Integrated Product Design)等多个顶尖项目的 offer。最终,她坚定地选择了心中早已认定的目标——宾大 IPD。
两年前,Alice 初次来到一只梨进行留学规划时,宾大的 IPD 项目便已是她心中的首选。与传统设计专业相比,IPD 所倡导的跨学科视角深深吸引了她:“它将设计、工程与商业融合在一起,强调从用户需求、市场环境到技术实现的全链路思考,真正推动产品落地。而我希望未来所设计的产品,不只是好看或好用,更能精准连接‘人——技术——市场’之间复杂而真实的关系。”
对 Alice 来说,选校从不是对名校的盲目追逐,而是一场关于匹配度和成长性的深度判断。这份务实清晰的认知,也贯穿于她一路走来的每一个选择之中。
回忆起康奈尔大学的本科生活,带给Alice的不仅是学业上的成长,还有内心的满足与喜悦。虽然许多人会调侃康奈尔所在的小镇Ithaca“偏僻”、“无聊”,甚至戏称为“村”,但Alice却认为,正因为这座小镇远离都市的喧嚣,她与朋友之间的关系才格外亲密与真挚。
在康奈尔的四年,Alice的大部分时光都与好友共同度过。她回忆说:“我们一起做饭、打牌,在学校的斜坡草地上野餐、看日落,去公园里烧烤、钓鱼、摘苹果。这种质朴、纯粹的快乐可能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很难实现。如果在纽约或哥伦比亚大学,我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时间和朋友们在一起,因为那里的学生步调更加繁忙。”
康奈尔独特的地理环境,也为Alice创造了高度专注的学习空间。学校与宿舍仅仅十分钟路程,即便在图书馆待到凌晨两三点,也十分安全便捷。Alice特别提到:“康奈尔的学习氛围非常好,同学们都特别努力。在这样的小镇,你的生活重心可能就是学习和朋友,非常简单纯粹。”
本科时期,Alice还经历了一次重要的换专业。她最初就读于DEA(Design and Environmental Analysis)专业,这个专业规模较小,学生与教授之间的互动非常频繁密切。然而,她发现自己的兴趣逐渐向交互设计、用户体验领域转移,最终果断转入了规模更大、方向更多元的Information Science专业。
尽管Information Science专业更偏重技术导向,课程规模大,与老师、同学的互动也相对减少,但Alice更加确定自己的决定:“转专业后,我学习的内容更加贴合未来职业方向,虽然人际互动不像之前那么密切,但我仍然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。”
如今,即将踏上宾大IPD这一崭新旅程的Alice,清晰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、该如何实现。对她而言,过去四年在康奈尔的沉淀与积累,以及与朋友们那些美好的日常,都会成为她未来前行路上最珍贵的养分。
一只梨导师
情绪充能站
“
一只梨对我而言,并不只是一个留学机构,而是一个‘可以喝咖啡聊情绪、也能陪我跑腿调研看展’的支持系统。
”
Alice本科主修信息科学,与许多同专业的同学一样,前两年以通识性的课程为主,内容偏向计算机科学的技术训练,包括编程、数据分析、网站开发、数据科学等。“我们学的内容其实跟CS专业挺像的,要掌握基本的编程语言、会写代码、学网页构建、理解工具逻辑……这些都为后续的学习打下了技术基础。”
真正打开她设计兴趣的,是大三大四阶段那些更加自由、方向明确的项目课程。完成了通识训练之后,她开始围绕自己的兴趣选择项目:“我做了很多面向少数群体的设计,比如一些可穿戴设备,也有APP和界面设计,甚至还结合硬件做了一些原型,比如智能手套、交互杯子……形式很丰富。”她认为,虽然形式多样,但所有项目都指向一个核心:以人为本的交互设计。“我更关注人和外界之间的关系,不管是通过软件还是硬件,我一直在想:人是怎么用它的?它又如何回应人?”
谈到是否一开始就决定申请美硕,Alice的回答很坦率,“我其实不是一个想要长期留在美国工作的人,所以对我来说,读研更像是一个创造实践与知识延展。”在她看来,本科四年更多是打牢基本功,比如进入大厂后能胜任基础开发或执行任务:“我可以完成他们交给我的功能开发、3D打印建模这些内容。”而硕士阶段则是一个可以深入研究特定方向、进行更具创造力实践的阶段——比如去探索特定群体的需求,尝试创新性的设计思路,甚至将个人研究延展成产品可能性。
从左至右:Cathy、秦老师、Alice
“我从大二下学期就开始为申请做准备。当时我开始跟一只梨这边接触,和秦老师沟通。”到了大三暑假,Alice正式确定选校方向,并开始规划申请节奏。尽管大三学业压力不小,她仍抽出时间持续推进作品集探索与申请准备。“整个申请主要集中在大三暑假到大四上学期这段时间,大概七八个月,时间还是很紧的。”
Alice坦言,在整个申请过程中,最大的挑战从来不是“能不能完成”,而是“如何做好自己”。尽管项目繁多、时间紧张,她依然为每个作品设定了明确的目标与节奏:哪些需要收尾、哪些正在启动;哪些需要合作、哪些独立完成。她与室友兼朋友Cathy每周固定见面一到两次,一起复盘进展、同步反馈。“我们经常在各自房间里用电脑熬夜‘搞事情’,但这种状态反而让我们感觉特别开心。”Alice笑着说道。
Alice并非从开始便规划好了每一步,但随着项目推进,她的目标逐渐清晰起来。选择一只梨留学做申请辅导,也正是因为与这里的老师“风格契合”和“聊得来”。起初,她是听一位学姐介绍过来的,后来发现好友Albert也在这里。“第一次聊天我就知道,这就是我想要的导师。”她不希望申请过程变成一场“冲刺KPI”的流水线式辅导,而是希望有一位真正理解她、愿意在她节奏下同行的伙伴。
“我是个典型的 P 型人格,经常拖延,情绪也会有起伏。”Alice 坦言。但在申请过程中,她从未感受到催促或压力。“文书老师从不逼我交稿,而是花很多时间跟我聊天,耐心听我讲想法、讲经历,努力理解我背后的动机和选择,然后我们一起把这些慢慢变成文字。”
许多她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潜在闪光点,往往是在一次次启发式对话中被挖掘出来。那些埋藏在潜意识里的细节与情感,最终也成为文书中最打动人的部分。“一只梨对我来说,不只是一个留学机构,更像是一个可以边喝咖啡边聊情绪、甚至能陪我跑腿调研、一起看展览的支持系统。”她笑着说。正是这些看似“非正式”的陪伴,构建了真正的信任感,让她感受到——这群人是真的在陪她一起,认真做一件重要的事。
这份情绪上的支持与理解,也帮助她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节奏。她很清楚,自己不是那种“标准模板型”的申请者,她始终坚持在每一次选择中,去确认“我是谁”、“我真正想做什么”。
哈佛面试磕绊
宾大才是梦校
“
我妈妈其实挺希望我去哈佛的,觉得它在简历上是无可替代的敲门砖。为了迎合,我也做了一些更‘符合哈佛口味’的作品。我当时感觉自己在做一些并不喜欢的事。甚至会有点做不出来,越努力反而越卡壳。
”
一开始,Alice 就将宾大 IPD 明确为主申项目,并以此为核心,围绕交互与产品方向,挑选了包括哈佛、加州伯克利、康奈尔 Tech 在内的一批顶尖项目。“其实这个领域能选的好学校不多,我们这一圈同学申的基本就是那几所。”她笑着说。
哈佛VS宾大
但在选校之外,来自家庭的期待也悄然影响着她的判断。哈佛,这个在许多中国家长心中象征着“顶点”与“荣耀”的名字,一度成为她努力“讨好”的目标。“我妈妈其实挺希望我去哈佛的,觉得那是简历上无可替代的敲门砖。”为了迎合这份期待,Alice特地做了一些更“符合哈佛口味”的项目——议题更前沿,形式更概念化。
然而,越是试图模仿“正确答案”,她越感到与自己本真的方向脱节。哈佛偏好抽象议题与实验性表达,哪怕脱离产品使用场景也无妨;而 Alice 内心真正相信的,是“落地”和“调研”的力量。她更习惯从用户出发,围绕真实的需求展开调研,再一点点推演出产品逻辑,而不是凭空创造一个看起来“天马行空”的装置,去承载一个遥远难解的议题。
“我当时感觉自己在做一些并不喜欢的事。甚至会有点做不出来,越努力反而越卡壳。”她坦言。在“成为什么样的人”与“别人期待你成为谁”之间的挣扎。
转折来自一次家庭与导师的“双重松绑”。家人向她表达了理解与支持,愿意尊重她对未来的判断;而一只梨的老师也鼓励她放下“学校喜欢什么”的执念,重新回到那个她最熟悉、也最擅长的创作节奏——聚焦于“你是谁”,而不是“你该成为谁”。
在这一调整下,Alice 重新梳理了自己的方法论。她根据不同学校的偏好做出细微调整,但作品集的主线从未改变。不是迎合,而是寻找适配;不是全盘重塑,而是基于自我价值的细节微调。渐渐地,她找回了创作的状态,也重拾了对自己的信心。
后来,哈佛真的发来面试邀请。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面试,她紧张到发抖,也因为毫无经验而“翻了车”。当招生官问她:“你最不喜欢的一个项目是什么?”她真的以为老师在问某个项目,认真地讲起了一段团队合作不顺的经历。她当时觉得回答得非常真诚,甚至看到面试官笑了。但事后复盘才意识到,那其实是一次典型的“读题失败”——招生官真正想听的,是你如何看待项目中的不足,以及未来如何改进,而不是一次消极情绪的回忆录。
这段经历她一直记着,不是出于失败,而是作为一种提醒:你不仅要知道对方在问什么,更要知道自己在表达什么。“我不是那种很擅长表演的人,也不太会揣测面试官的心理。”她说,“但也许正因为后来我做的每个选择都更贴近自己,所以最终才被我最想去的学校看到。”
她没去哈佛,但最终走进了最心仪的宾大 IPD。而这一路,从试图讨好,到坚定做自己,是 Alice 在申请季中最艰难、也最珍贵的收获。
藤校喜欢
什么样的学生
“藤校喜欢我这样的!”
谈到名校的偏好,Alice显得格外笃定。这种自信不是炫耀,而是一种源自内心的清晰感。她深知,藤校从不追求“完美模板”式的申请者——他们真正欣赏的,是那些拥有独特经历、明确方向,并愿意在自己所选择的路径上持续投入的人。
宾大面试那天的场景,她至今记忆犹新。正式问答结束后,她主动向招生官抛出了一个问题:“藤校的名额如此有限,而中国学生又如此优秀,你们到底是如何做筛选的?会不会觉得大家看起来太像了?”
招生官的回答让她印象深刻:“我们从不会在‘整体优秀’的人群中挑选谁更强,而是在每个人的‘不同点’中寻找独特。即便都是来自中国,但每个人的背景和关注点都不一样——有人有美国本科经历,有人来自综合性大学;有人偏技术,有人偏设计;有人关注人工智能,也有人研究气候议题,还有人,像你一样,致力于少数群体的需求。”
那一刻,Alice 豁然开朗——真正打动名校的标准,不是你有多“全面”,而是你是否足够真诚地走在自己所选择的方向上。她的设计始终围绕“人”展开:可穿戴设备的开发、边缘群体的使用调研、基于真实需求的行为分析……她并不执着于概念是否前卫,也不热衷于炫技,而是坚持从使用者出发,深度回应现实问题。“对我来说,设计不是为了自我表达的形式游戏,而是理解与连接的工具。”她说,“一个项目是否有价值,关键不在于形式多酷、技术多新,而在于你能不能清楚地回答:我为什么做它?它要解决什么问题?它的重要性在哪里?”
“我不是来混文凭的,
我是真心希望有所作为。”
在她看来,顶尖名校项目真正看重的,并非花哨的模型或炫技的表达,而是你是否拥有一个清晰、聚焦的中心议题。你知道自己要研究什么、来这里是为了什么——靠近哪些资源、达成怎样的目标。真正稀缺的,从来都不是能力,而是这份明确的主动性。
“藤校并不神秘。真正重要的是,你是否愿意花足够长的时间,确定一个属于自己的方向,并忠实地走下去。哪怕这条路不够热门,哪怕无法取悦所有人。”她说完,语气温和,却多了一份令人信服的坚定。
父母教给我的
为人之道
“
我觉得我爸妈都是那种特别难得的人—— 没有什么明显缺点,很纯粹地在过一种他们认为值得的生活。
”
当我问 Alice:“你为什么会多买一杯奶茶?是家庭教育的影响吗?”她笑着回答:“我觉得是受到我妈妈的影响。她是一个非常热情、也总能顾及他人情绪的人。从小她就教我多替别人着想,比如要提前准备一些东西。所以我会想,会不会还有老师没点单?会不会临时有学生来上课?多买一杯,大家就不会觉得尴尬了。”
这样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,却恰恰映射出她性格中那份稳定而温柔的底色——体贴、敏锐,总愿意为他人预留空间。这种对情境和他人感受的高度感知,不是刻意为之,而是在潜移默化的家庭氛围中自然养成的本能反应。
Alice 的妈妈是一位医生。她不只是看病,而是在全力以赴地帮助每一个人。她几乎每天都工作到凌晨一两点,除了日常门诊,还会主动维护病友群,定期追踪病情、耐心解答疑问。她的付出早已超出“职责”本身,更像是一种持续的、发自内心的承诺。
Alice说:“我妈妈是我见过最努力、也是非常要强的人。她肩上的责任很多——不仅是医生,还是老师,要带学生;也是科研工作者,要做研究、分析病例、探索药物原理。她为了把每件事做到极致,可以牺牲自己的时间、睡眠,甚至生活质量。人们尊重她、佩服她,不只是因为她的能力,而是因为她对工作的热爱和极强的内驱力。她做事没有私心,也从不偷懒,总是全情投入地去做对的事、对社会有价值的事。”
妈妈的努力从不张扬、不诉苦,也不索求回报。她安静而坚定地热爱着自己所做的一切——这份力量,本身就是一种最深沉的教育。
Alice爸爸跟她妈妈性格不太一样,他同样非常努力工作,但对Alice影响最大的是父亲的正直。Alice 说,“我爸本身就很聪明,技术出身的他思维非常敏锐。但比聪明更重要的,是他始终坚持原则,不会被外界环境或诱惑动摇。他总是坚持自己的初心——如果他认定要做一个产品,就会全身心投入,不是为了赚钱,而是为了把事情做到极致,让公司变得更好,带领团队把产品做出来。”
“作为一个设计师,我很能共鸣他这种‘做到最好’的状态。我爸他对生活也是非常专注,只有两件事:家庭和工作,几乎没有其他的干扰。”Alice 笑着说:“我觉得我爸妈都是那种特别难得的人——没有什么明显缺点,很纯粹地在过一种他们认为值得的生活。”
因此,父母对Alice的影响,总是让她不自觉地将目光投向那些被忽视的人群。哪怕这些选题未必能为申请“加分”,她仍愿意投入大量时间去理解、去调研,只为确保使用者的真实感受被看见、被照顾。在她看来,设计的意义并不在于界面是否够美观,而在于它是否真正让人感到舒适、自在。
这份以人为本的初心,不仅塑造了她作品的气质,也塑造了她渴望成为的交互设计师。
采访接近尾声时,我问她:“如果撇开申请和项目,这一年你最大的成长是什么?”
Alice沉思片刻,说道:“我学会了用不同的角度看待他人。以前我觉得某个功能很酷,某个界面很美,但用户可能根本不在意。很多我以为的‘创新’,其实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。现在我在做设计时,很难再只想着‘我想表达什么’,而是会首先去问:用户真的需要吗?他们会使用吗?这个设计,对他们真的有意义吗?”
过去,她的设计出发点总是“我”:我想表达什么、我想解决什么问题、我认为怎样才是好的设计。但这一年,她走进了更多真实的生活场景,接触到了各种被忽视的用户,与他们对话、共情,逐渐打破了以自我为中心的视角。她开始意识到,设计不仅是一种技能,更是一种视角的转换。许多时候,决定一个设计价值的,不是它是否够新、够炫,而是你是否真正“听见”了用户的声音。
过去11年,一只梨选择深耕交互设计这个垂直赛道,很多人觉得小众,但如今的趋势,正印证了这个判断的前瞻性。11年来,一只梨帮助数百位学员,实现设计梦想。
以全球交互No.1的CMU为例:国内数量最多(总数30位+),人称“卡梅大陆承包商”。
藤校每年都稳定有20个左右案例。宾大IPD全国录取5人,其中4人都出自我们机构。
一只梨在本科申请上都是纽大、伦艺成果以上100%录取。
创始人15年亲自在一线教学,且被上海交大、清华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同济大学、西安美院等聘任的校外导师。
如果你也在纠结选校、转专业、作品集、申博规划,不如来聊一聊。也许,你命中注定的那所Dream School,正在悄悄等你发现。
| End |
编辑 | 一只梨
图片 | 官网/一只梨/网络
作品及图片版权归设计师本人和所服务企业所有,
未经允许转载挪用,虽远必🐷
发布于:陕西省象泰配资-配资证券网-配资交易网-配资平台查询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股票杠杆炒股不同于依赖供应商的传统模式
- 下一篇:线上配资网址串联时机学习新知识时